
- 全站推荐
- 全站置顶
- 首页推荐
- 社区推荐
-
置顶推荐
- 6小时
- 12小时
- 24小时
- 3天
- 一周
- 长期
- 设为精华
- 热门推荐
- 撤销审核
- 进小黑屋
- 生成议题
距离上一篇文章《自动驾驶地图的合规维度 - 资质篇》已经过去了快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不少事情。
上一篇说过,小鹏收购江苏智途公司以获得甲级测绘资质,希望自己测绘高精地图,不再依赖高德这个第三方。
然而时至今日,智途公司的甲级资质依然没能通过复审换证,小鹏自己测绘高精地图的计划暂时搁浅。

封闭路段的高速 ngp 对于高精地图的更新频率要求较低,依赖高德暂时没有影响这个功能的正常使用。
然而在城市 ngp 的推广上,小鹏遭遇了因为高精地图的审批的阻力。支持城市 ngp 功能的小鹏 P5 车型,自 2021 年 4 月发布,直到 2022 年 10 月,才在广州率先开放了城市 ngp 功能。按照计划,在今年上半年 P5 的城市 ngp 才刚刚能在上海、广州、深圳的部分道路使用。

可能正是看到了依赖高精地图方案的审批慢、成本高的缺点,叠加 tansformer+BEV 的火热,今年包括小鹏在内的一些车企,以及包括元戎启行在内的智驾供应商,都宣称将打造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方案。
本篇文章将继续上一篇的话题,聊聊为什么高精地图审批这么麻烦,以及对于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方案来说,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审批的障碍了?
地图不是测绘了就能用
上一篇梳理了自动驾驶地图的测绘资质问题,但光有了资质并不是意味着可以随便使用测绘的地图。在地图测绘下来之后,还涉及地图的汇交和审批。
我们先从大的测绘管理制度来讲,由广及细。
测绘分为基础测绘、界线测绘和其他。
基础测绘就是对地理进行基础性的绘制,构建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一切的测绘活动都是基于基础测绘成果之上的,基础测绘是公益性事业,由国家组织进行。
界线测绘就是国家国界、省界、市界等行政区域边界的测绘,也由国家相应的主管部门进行组织。其他测绘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其他领域的测绘活动,就包括我们所说的自动驾驶地图。
《测绘法》规定,我国施行测绘成果汇交制度,属于基础测绘成果的,汇交副本;非基础的,汇交测绘成果目录。汇交的目标单位,是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原来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现在是“自然资源部”。
如果测绘成果涉密,还应当执行国家的保密制度,判断测绘地理信息的涉密标准,可以参考自然资源部和国家保密局印发的《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

作为测绘成果的“地图”,还应当执行我国的地图审核制度。凡是要向社会公开的地图,都应该报自然资源部审核。由自然资源部审核通过并标注审图号,方能使用。
上一篇梳理过,按照 2016 年颁布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强自动驾驶地图生产测试与应用管理的通知》,自动驾驶地图属于导航电子地图的组成部分,因此自动驾驶地图还应当符合导航电子地图的特别管理规定。由于当时认为自动驾驶地图对于地图数据信息的精确度要求非常高,于是通知中还要求把这些自动驾驶地图数据按照涉密测绘成果进行管理。结合《地图管理条例》的规定,自动驾驶地图还应当经过保密技术处理,方能投入使用。
于是,自动驾驶地图的管理,又能追溯到 2007 年颁布的《国家测绘局关于导航电子地图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以及 2012 年颁布的《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保密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两部文件对于导航电子地图的保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测绘资质单位要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涉密测绘成果资料的安全。未经省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保密技术处理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属机密级国家秘密资料。各单位必须按照公开地图内容表示、基础地理信息公开表示、遥感影像公开表示、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等有关规定与标准,正确表达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内容,并依法报送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进行保密技术处理。未经保密技术处理的数据主要应用于导航电子地图的生产和制作工作,如需向其他的部门或单位提供使用,必须依法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未经批准,一律不得擅自提供。
汇交、地图审批、保密技术处理,经过这些审核程序之后,自动驾驶所需的高精度地图方能投入使用。
国家安全
从 16 年的这份《关于加强自动驾驶地图生产测试与应用管理的通知》的文件内容来看,管理部门当时对于自动驾驶地图的态度还是比较紧张的。 16 年还处在一个算力有限、激光雷达巨贵的时代,可能正是由于当时传感器能力有限,使得自动驾驶技术对于地图精细度的要求更高。更高的测绘精度,使得监管部门更加谨慎,于是也提出了更高的保密要求。
过于精确的地图信息,可能会暴露我国的重要军事设施、道路、敏感地区的具体方位,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有必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具体的处理方式,参考《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GB 20263-2006 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城市高精地图的审批相比于封闭路段更加困难?实际上上海的内环高架、延安高架这些经过市区核心地段的封闭路段,也有高精地图覆盖,并且目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关于这一点,笔者的理解是,封闭路段,并不能直接将路线导向特定的目标,我们从高架下来,还得走一段城市路段,才能到达特定的地点。所以,封闭路段一般不会构成对于特定地点的明确指向,必须和下高架之后的城市路段相结合,才能完成最终的指向作用。而且封闭路段大部分是高架,是环绕市区建筑物运行的,测绘过程中只要剔除建筑物的具体信息,即可完成对建筑物的加密,建筑物本身的特点、方位、外形结构都不会影响封闭路段高精地图的路线。
城市高精地图的复杂度在于,增加了各个具体的路口、道路标识、红绿灯情况、城市小路的信息,这些信息很容易指向某个目标地点、小路的轮廓可以描绘一个建筑的轮廓和范围、各种标识可以和其他信息相结合对一个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推测。总而言之,城市道路的信息量更大,有更多可以作为定位的参考信息,所以保密的要求更高,加密的方式更苛刻。因此,审批和处理周期会更长。
监管逻辑:不依赖高精地图就不用审批了么?
其实城市高精地图的审核只是这个方案的其中一个问题,从产品层面,城市高精地图由于包含的信息很多,对于智驾来说,对地图信息的实时更新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一段高速可能一个月都不会改变什么,但城市的施工、改道,可能一周一变甚至一天一变。对于依赖城市高精地图的智驾方案来说,需要花大量的成本保持地图的更新,无论是对于自己测绘还是直接用供应商,这个成本都很大。
现在的芯片算力、摄像头像素、激光雷达线数,已非 16 年所能比拟,使得不依赖高精地图,仅凭传感器实时绘制路况信息成为了可能。那么是不是脱离了高精地图,仅靠车辆自带的传感器来实时测绘路况,就能避免审批程序了呢?

22 年 8 月,自然资源部发了一份《关于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通知》,里面说道,“智能网联汽车安装或集成了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模块、惯性测量单元、摄像头、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后,在运行、服务和道路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空间坐标、影像、点云及其属性信息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规定的测绘活动,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规范和管理。”
采集、储存、传输、处理,这四个词包含的范围尤其大,已经把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方案,也囊括进去了。
“需要从事相关数据收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的车企、服务商及智能驾驶软件提供商等,属于内资企业的,应依法取得相应测绘资质,或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应测绘活动;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应测绘活动,由被委托的测绘资质单位承担收集、存储、传输和处理相关空间坐标、影像、点云及其属性信息等业务及提供地理信息服务与支持。”
似乎各个车企、供应商,好不容易从测绘资质的难关里要出来了,这一纸文件又把他们拽了回去。各家下半年要脱离高精地图的辅助驾驶方案,似乎都必须在获得甲级测绘资质之后,才能推出。
从这份文件也可以看出主管部门目前的态度,目前还没有考虑针对自动驾驶地图单独设立一种资质,尽量在不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把自动驾驶活动往“导航电子地图”里面装,哪怕不是在测绘地图,你汽车通过车辆上的各种传感器实时收集的数据,也要纳入到这个箩筐里面来进行监管。
立法建议:明确定义、兼顾发展
自然资源部的这份文件,适用的对象是“智能网联汽车”,那么到底什么是智能网联汽车?我们日常所开的带辅助驾驶的特斯拉、理想、小鹏,都算不算智能网联汽车?
在之前的文章里,笔者专门就“智能网联汽车”的定义进行过梳理,在工信部发布的文件中,“智能网联汽车”仅指具有 L3 及以上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我们日常使用的辅助驾驶功能只能算 L2 ,不能算在“智能网联汽车”的范围内。
但工信部发布的文件的性质,是部门规范性文件,自然资源部作为不同的部门,可以在自己的规范性文件中,作出不一样的定义。
在《关于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通知》中,自然资源部并没有进一步解释里面提到的“智能网联汽车”的具体定义,仅提到“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智能汽车、网约车、智能公交以及移动智能配送装置等)”。那么这里的“智能汽车”,又是否包含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呢?
在 2020 年由自然资源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中,将“智能汽车”定义如下:
“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通常又称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这里的自动驾驶功能,是否包含我们日常所用的“辅助驾驶功能”?这里并不明确,仅通过这样的定义,很难判断。从明确的驾驶自动化等级划分来说,自动驾驶仅指 L3 级以上的能力;但如果把“自动驾驶功能”仅理解为一种“技术”,则辅助驾驶作为一种 L2 级的“驾驶自动化”,也可以从文义上被纳入到这个范畴里。
纳入与不纳入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如果辅助驾驶功能也算在“智能汽车”里,那么特斯拉 FSD 、小鹏的 XNet 、元戎启行的 DeepRoute-Driver 3.0 这些哪怕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能驾驶方案(辅助驾驶),都会面临测绘资质的要求。如果没有测绘资质,则难以向消费者推广运用。因为消费者日常一旦开启智能驾驶,车上的传感器就一定会开始采集或者处理路面信息。
如果不纳入,那么从文本逻辑上看,比较符合现状。特斯拉的 noa 也不依赖高精地图,但目前是可以稳定运行的,暂时并没有被提出要获得测绘资质(也获得不了,因为负面清单)。但从监管的立法本意来看,这样的口子应该是早晚要关上的,毕竟现在的小鹏、特斯拉还有一些智驾供应商,实际上做的就是“自动驾驶”研发的事情,不能说做的只是“辅助驾驶”就能逃避监管。
从逻辑的完善来说,笔者是支持统一明确定义的,把“辅助驾驶”,也应当囊括到“智能汽车”的范围内。但笔者对于把不依赖高精地图的智驾方案,一箩筐装进“甲级测绘资质”里面,持有保留的态度。理由有三:
其一,满足智驾需要的数据是很模糊的,不需要很详细地识别出前面的是什么车、什么人、什么建筑、什么部门,这些具体信息对智驾是没有意义的。智驾的运行只要知道前面的是行人、轿车、卡车、车道线、红绿灯,它只需要描绘出一个轮廓,就足够了;

其二,智驾是不需要记录详细的路线、地理信息的。目的地是人类设定的,智驾不需要参与,更不需要知道目的地是什么样的地方。智驾的训练不需要记录详细的路线和地图,也不会产生具有导航功能的结论。现在的一种训练方式,是直接把识别到的内容,做成模型,用超级计算机仿真模拟出一个新世界,让自动驾驶软件进去练习,可见现实的路线只有成为素材的意义;

其三,加密、脱敏目前在技术上已经不是难事了。对智驾来说,唯一可能涉及到保密、敏感信息的过程,是对视觉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和系统识别的信息、结论进行比较、校准的过程。视觉摄像头记录的内容需要比较完整,才能看出是哪些因素干扰了识别结果,并标注出准确的定义。对视觉摄像头记录的画面内容,应当纳入监管的范围,并且进行加密、脱敏,其实这个过程目前在技术上并不难做到。

总而言之,应该看到,智驾的训练、运行,和“测绘”,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对数据的要求、筛选、应用,是完全不同的,监管最好能够“因地制宜”。如果一味地用“甲级测绘资质”来管理,对于目前的一些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对技术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笔者依然觉得,未来应该针对“自动驾驶”的实时绘制,能单独设立一种门槛较低的测绘资质,既能满足测绘制度的监管,不破坏大的制度结构,也能兼顾企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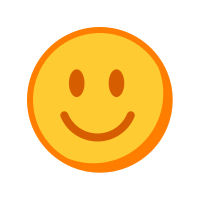



 积分赞赏人员
积分赞赏人员
 添加咨询车型
添加咨询车型









 新出行
新出行
 {{data.limitTimeActivitySearchKeyword}}
{{data.limitTimeActivitySearchKeyword}}